白鯨記(紀念梅爾維爾200歲冥誕,全新中譯本)
作者:赫曼•梅爾維爾
1819年生於美國紐約市,1837年因家境緣故自奧爾巴尼學院輟學,之後曾經務農、從事過一般職員及小學教師等工作。1841年起接續在捕鯨船與遠洋商船上擔任水手,經過數年海上漫遊返國後,1845年起投入寫作,頭五部長篇小說讓他成為頗受歡迎的冒險小說家。接著他以海上生活經驗開始構思第六部長篇《白鯨記》,這部小說花費17個月才完稿並於1851年出版,然而首刷1000本於出版後首年竟只賣出5本,其餘庫存因倉庫失火而遭焚毀。由於此後的長短篇小說銷售不佳,他於1860年代後期轉而寫詩,但已無出版商願為其詩集提供預付版稅,只能自費出版。1891年,梅爾維爾潦倒以終,逝世於紐約。
譯者:陳榮彬
國立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曾三度獲得「開卷翻譯類十大好書」獎項,近作《昆蟲誌》獲選2018年Openbook年度好書(翻譯類),已出版各類翻譯作品50餘種,近年代表性譯作尚包括海明威經典小說《戰地鐘聲》,還有《火藥時代》與《美國華人史》。曾任第41屆金鼎獎評委。
※ ※ ※
這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對決!
「叫我伊什梅爾吧。」
故事以捕鯨船水手伊什梅爾這句舉世聞名的開場白作為開頭,呈現出人類以己身的力量去對抗大自然的過程。小說中的白鯨莫比敵就像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大自然的生態。它呈現悲觀和神祕的情感色彩,轟動歐美文壇。
這是一個漫長而驚險的故事,一個關於大海、關乎人性的故事。《白鯨記》結合了虛構與寫實兩種寫作手法,梅爾維爾用敏銳和感性的視角社會,通過小說來表達自己對整個社會生活和人類心靈的思考與評價。
※ ※ ※
叫我伊什梅爾吧。多年前,姑且別管到底是幾年前,我的包包裡沒有多少錢,也可說是身無分文,而且陸地上也沒有特別讓我感到有興趣的人事物,於是我想自己該登船雲遊四海一番。這是我排憂解悶、疏通氣血的一種方式。每當我的嘴型變得猙獰了起來,每當我的靈魂好像置身陰雨潮溼的十一月天,每當我發現自己在棺材店前會不自覺停下腳步,且遇到送葬隊伍就會從後面跟上去,尤其是每當我的憂鬱症犯得格外嚴重,必須憑藉強烈道德感才能壓抑內心衝動,讓自己不要刻意上街去把行人的帽子給一頂頂打落──每當這些狀況出現時,我就知道自己又該儘快出海了。這是我避免讓自己吞子彈的替代方案。加圖以刀劍自殺前,暢讀哲學經典,而我沒自殺,只是悄悄登船出海。這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只要能了解這種狀況,幾乎所有人遲早都會跟我一樣珍惜自己對大海懷抱的那種情感,只是珍惜的程度各自不同。
我們這島城曾是曼哈托人的居住地,四周被碼頭環繞,就像印地安群島被珊瑚礁環繞一樣,如今環繞包圍著它的,則是商業的浪潮。不管往右或往左,每一條街道都通向海邊。下城的盡頭就是砲臺,那裡的防波堤被海浪沖刷著,涼爽微風吹過,幾個小時前在陸地上都還看不見風與浪。看看現在,那裡已有一群群欣賞海景的人。
在這如夢似幻的安息日下午,到城裡去繞一趟吧。從柯里爾海岬走到康恩提街,然後在白廳街往北走。你會看到什麼?成千上萬的人站著呆望大海,他們遍布城中,好像沉默的站崗哨兵。有人倚著樁子,有人坐在碼頭前端,有人遠眺著那些中國船隻的舷牆,也有人高高地站在索具上,好像站得越高就能看到越好的海景一樣。但這些都是陸地上的人,平日被禁錮在泥糊的木屋裡,離不開櫃檯邊,不得不坐在板凳上,或是鎮日案牘勞形。那麼,這是什麼情況呢?沒有綠色的田野可以看嗎?他們在這裡幹麼?
看哪!人越來越多了,直接往海邊走去,像是要跳進海裡一樣。怪了!只有走到陸地盡頭,他們才會心滿意足,光是到那些倉庫的背蔭處閒逛一番,是不夠的。當然不夠。只要不掉進海裡,他們就會想盡辦法靠近大海。他們站成一列長達數哩的隊伍,全都是內陸居民,住在大街小巷中,來自四面八方。但他們全都群聚在此。您說,會是船上羅盤指針的磁力把他們吸引過來的嗎?
再舉個例子。比方說,你人在鄉間某個湖區的高地。隨便選一條路,十之八九都會帶你走向某個溪谷,眼前出現溪邊的一個小水潭。這真的很神奇。隨便挑一個心不在焉、正在沉思冥想的人,只要他雙腳一站,跨出腳步,肯定都可以把你帶往水邊,如果那一帶的確有水的話。若是行經美國這個大沙漠時,你覺得口渴了,車隊裡又剛好有一位鑽研形上學的教授同行,就可以做這個實驗。沒錯,沉思冥想與世上的水總是結合在一起的,這是眾所皆知之事。
假設有個藝術家打算為你作畫,把浪漫的薩科河谷景致畫成最夢幻、最隱蔽、最安靜、最誘人的作品。他使用的主要元素會是什麼?畫裡會有一棵棵空心的樹,像是裡頭有隱士和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受難聖像,這邊畫了一片草原,那邊有一群牲口,遠方的小屋有一縷炊煙升起。遙遠的林地裡,一條錯綜複雜的小徑往深處蜿蜒,通往層層交疊的一片山脊,山坡如此青翠。但是,儘管這畫面讓人看了出神,儘管松樹發出沙沙聲響,像落葉掉在牧人頭頂的聲音一樣,除非牧人的眼睛緊盯著眼前的奇幻小河,否則一切都是枉然。六月時去一趟大草原,你會有幾十哩的路程都在及膝的虎皮百合叢中跋涉,但唯一欠缺的是哪種吸引人的事物呢?是水──那裡沒有任何一滴水!如果從尼加拉瀑布奔流而下的是滾滾黃沙,你還會不遠千里到那裡去欣賞嗎?那可憐的田納西州詩人,在突然拿到兩把銀幣時,為什麼還需要考慮自己到底該買一件大衣(這是他迫切需要的),或該把錢當成旅費,徒步前往洛克威海灘?為什麼幾乎每一個身心健全茁壯的青年遲早都會想去看海,想到發瘋?為什麼當你初次以旅客的身分搭船出海,聽說船已駛離、看不到陸地時,內心會感到一陣莫名的激動?為什麼古波斯人認為大海是神聖的?為什麼希臘人認為海裡有海神,就像天上也有天神那樣?這一切當然都不是沒有意義的。而且,更加具有深意的,是美少年納西瑟斯的故事:他因為愛上了自己在水中的柔美倒影而飽受折磨,最終投水溺斃。我們一樣也會在河面與海面上看到自己的倒影。那是一種無法掌握的生命幻影。而這就是一切的關鍵。
每當我的眼睛開始變得迷濛,我的肺部開始太過敏感時,習慣上我就會出海去,不過我的意思不是說我曾以旅客的身分出海。因為,旅客必須有行囊,如果行囊中空無一物,它不過就是一條破布罷了。此外,旅客會暈船、會吵架,晚上不睡覺,一般而言他們在海上無法自得其樂──不,我不曾以旅客的身分出海;但是,儘管我還算是個有經驗的水手,我也沒當過船隊司令、船長或者廚師。我把殊榮與聲譽都讓給了喜歡那些職務的的人。我討厭一切崇高可敬的苦工、考驗與磨難。最多我也只能把自己照顧好,要我去照顧那些大船、三桅帆船、雙桅帆船或者雙桅縱帆船什麼的,我可辦不到。至於廚師,我承認那是個很體面的差事,也算是船上的幹部,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不曾想過自己會去烤雞燒鴨──不過,任何雞鴨要是能抹上適量奶油,食鹽與黑胡椒也都撒得恰到好處,就算不能說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可是會比任何人都更敬重那些雞鴨的。古埃及人對於燒烤朱鷺與河馬不也是滿懷崇敬與喜愛嗎?你看,金字塔不就等於是朱鷺與河馬木乃伊的巨大烤箱?
不,每次出海時,我總是當個普通的水手而已,站在船桅前方,鑽進艏艛,高高地爬到頂桅的頂端。沒錯,總是有人命令我做這做那,從這根圓杆跳往另一根,簡直像是五月草原上的蚱蜢。一開始,這種事讓人深感不悅。這種事挺傷人自尊,特別是對於那些世家子弟而言,像是來自范.倫塞勒、蘭道夫或者哈德克努特等家族的人。最糟糕的是,假使你曾當過意氣風發的鄉村教師,就連最高的男生站在你面前都還要戰戰兢兢的,如今卻要幹那種把手伸進柏油鍋的粗活。我敢說,從小學老師到水手的角色轉變肯定是非常難熬,如果欠缺塞內卡與斯多噶學派哲學家的堅毅秉性,是不可能咬牙苦撐過去的。不過,再怎麼難熬,只要時間一久,那種感覺也會變淡。
假設有船長手下的粗暴老頭命令我拿掃把清理甲板,那又怎樣呢?我是說,如果我把這種丟臉的事拿來與《新約聖經》裡的種種事蹟拿來相較,根本算不了什麼。即便我很快就乖乖服從粗暴老頭的命令,難道大天使加百列就會看不起我嗎?這世上有誰不是奴隸?你倒是說說看。那麼,無論粗暴老頭對我下達什麼命令,無論他們對我如何拳打手捶,我總是感到心滿意足,因為我覺得這沒什麼,因為我知道,不管是從形而上或形而下的觀點看來,其他人差不多也都是這樣被對待的。所以,這種被捶打的情況在船上司空見慣,所有船員都該相濡以沫,為此感到滿意。
再說,我之所以總是出海當水手,是因為我幹活就有錢拿,至於旅客,我可沒聽說過他們可以領到半毛錢。相反地,他們必須自己付錢。在這世界上,付錢與拿錢可說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在那兩個偷摘果子的賊遺留給我們的苦難裡頭,付錢這件事或許是最令人感到不舒適的。但若是拿錢,還有什麼事能與其相提並論?儘管我們衷心相信「錢財乃萬惡淵藪」的說法,也認為有錢人絕對進不了天堂,但收錢實際上卻是一種高雅而美妙的人類活動。啊!為了錢,我們就算下地獄也心甘情願!
最後,我之所以總是出海當水手,是因為活動筋骨有益健康,而且艏艛甲板上的空氣是如此純淨。因為,海上的風大多是往船首吹來的頂風,從船尾吹來的較為少見(不過,如果你違反畢達哥拉斯的格言,那風就會都跑到肚子裡了!),所以船上空氣都會先經過艏樓的水手,船長在船尾甲板上呼吸到的都是二手空氣。船長以為空氣是自己先呼吸到的,實則不然。同樣的道理,老百姓在其他許多事務上也都領導著他們的領袖,領袖卻幾乎不自知。但既然我已經屢屢嘗過大海的滋味,多次身為商船水手,為什麼還會想要踏上捕鯨之旅?最能回答此一問題的,莫過於命運之神,因為祂們總是像個看不見的警官那樣監視我,偷偷跟蹤我,以某種莫名其妙的方式影響我。而且,毫無疑問地,我會踏上這趟捕鯨之旅,也是出於早已注定的偉大天意。在其他一齣齣彷彿重頭戲的要事之中,此趟旅程只能算是某種簡短插曲與獨角戲。如果把這種狀況寫成一張節目單,肯定會是如此的模樣:
「美國總統大選,戰況激烈。」
「伊什梅爾出海捕鯨。」
「阿富汗血腥戰役。」
如果說命運之神是劇場經理,我還真不明白祂們為何要安排我擔綱這齣捕鯨戲碼裡的三流角色?而其他人又為什麼能當崇高悲劇裡的主角、風雅喜劇裡的輕鬆配角,或是滑稽劇的丑角──我還搞不懂確切的緣由為何。不過,既然我還想得起種種情況,我應該多少可以看出這是怎麼一回事:儘管這件事背後有許多動機與目的,但它們卻被巧妙地掩藏了起來,除了誘使我去扮演那個角色,還哄騙了我,讓我誤以為自己是憑藉著毫無偏見的自由意志與精湛判斷力而做出選擇。
其中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去看看那讓我難以抗拒的大鯨魚。那種可怕又神祕的怪物讓我好奇不已。其次則是牠那海島般龐大身軀翻滾於其中的狂野遠洋,而鯨魚為人們帶來的種種凶險狀況,全都難以言傳與名狀;伴隨著捕鯨之旅而來的千百種巴塔哥尼亞高原神奇景觀與聲音,促使我完成自己的心願。如果是別人,也許不會因為這樣就被打動,但對我來講,那發生在世外天地的一切總是讓我心癢難耐。我喜歡航行在禁海上,在只有野蠻人的海邊登岸。儘管我不會錯過美好的一切,我也很想見識一下那鯨魚有多可怕,而且只要牠們願意,我仍然可以和牠好好相處──因為,無論身在何方,我們最好都要與同伴好好相處。
基於以上種種理由,我才會欣然踏上這趟捕鯨之旅。於是,在那個奇妙的世界向我敞開之後,就像一個龐大水閘被打開似的,在狂想中,我任由一對對鯨魚漂進我的靈魂深處,彷彿無止盡的鯨魚隊伍,其中有個戴著頭巾的龐大幽靈,像是高聳空中的雪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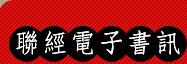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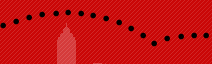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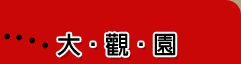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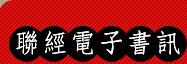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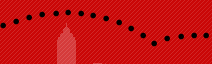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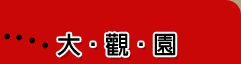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